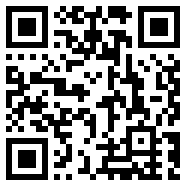假如说马来西亚的美食是 “热量炸弹” 界的顶流,没人会对立 —— 喷香的椰浆饭淋着 sambal 酱,沙爹串浸满花生酱,就连看似清新的啰喏(rojak)都藏着厚厚一层虾酱。但风趣的是,这个被 热量“围住” 的国度,却悄然藏着一群运动狂魔。
先别急着拿 “肥壮率” 说事 —— 没错,马来西亚的肥壮问题确实像加了双倍炼乳的拉茶相同显眼(世界卫生安排数据显现成人肥壮率超 30%),但这恰恰反衬出另一个本相:在油炸小吃和冰镇饮料的夹击中,大马人对运动的酷爱简直是一场 “绝地反击”。而这场反击战里,最嘹亮的号角,当属羽毛球。
羽毛球在马来西亚的位置,堪比海南鸡饭里的姜蓉 —— 缺了它,整个 “文明套餐” 就没了魂灵。12.19% 的参与率意味着:每 8 个大马人中就有 1 个会挥拍,小区空地上永久有人在打 “野球”,连咖啡店门口的停车位都或许被暂时改成球场。更甭说那些刻在国民记忆里的姓名:上世纪 90 时代的西迪兄弟(Sidek Brothers)像一阵旋风,把奥运奖牌第一次带回马来半岛;而李宗伟(Datuk Lee Chong Wei)更是把羽毛球打成了 “国民崇奉”—— 他的竞赛能让全国商铺提早关门,连总理都会发推文为他加油。当这位 “无冕之王” 在 2016 年里约奥运男单决赛中再次惜败林丹时,全马的叹息声估量能把双子塔的玻璃震出裂纹。
但假如你认为大马人只爱羽毛球,那就像认为 “怡保沙河粉” 只要一种做法相同单纯。当咱们把目光从球场移开,会发现更风趣的画面:穿长袍的马来阿姨在公园慢跑,华裔大叔骑着改装自行车络绎在组屋区,印度小哥戴着头巾在河滨拉伸 —— 这些场景,正在悄然改写人们对 “东南亚懒人” 的刻板形象。
在马来西亚谈跑步,得先承受一个魔幻实际:这儿的交通状况,能把急性子逼成哲学家。吉隆坡的早顶峰,摩托车能像泥鳅相同钻进轿车缝隙,而轿车则堵得能让人在车上泡好一杯拉茶。但美妙的是,正是这种 “移动困难症”,反而催生了跑步热潮 ——10.66% 的参与率,让跑步稳稳坐上 “国动老二” 的宝座。
大马人的跑步逻辑很简单:已然开车半小时挪 1 公里,不如穿上跑鞋直接 “开挂”。清晨五点的吉隆坡湖滨公园(Lake Gardens),简直是跑步爱好者的 “大型团建现场”:穿速干衣的年轻人冲刺,戴草帽的老人家慢走,甚至有推着婴儿车的爸爸妈妈一边跑一边给孩子唱马来童谣。最绝的是那些 “才智型跑者”—— 他们专挑堵车最严峻的路段跑,比方安邦路(Ampang Road),看着路周围堵成长龙的轿车,跑着跑着就笑出了声。
跑步在这儿不仅是运动,更是交际暗码。槟城的 “乔治市夜跑团” 会沿着海滨栈道奔驰,跑累了就钻进路周围摊,用一碗亚参叻沙(asam laksa)弥补能量;马六甲的 “榴莲跑” 更绝 —— 跑完 5 公里,结尾直接摆上整桌榴莲,美其名曰 “用运动抵消卡路里”。有位跑者在交际渠道吐槽:“本来想瘦身才跑步,成果每次跑完都被队友拉去吃炒粿条,现在体重没降,却是把全马的夜市吃了个遍。”
更有意思的是跑步与文明的磕碰。在开斋节期间,一些Mosque会安排 “晨跑 + 开斋” 活动,Muslim们跑完步,团体在寺前享用椰枣和粥;而阴历新年前后,华人跑团会戴着赤色发带跑步,结尾还会派发橘子 —— 究竟,“跑得多,赚得多” 的谐音梗,在哪都吃得开。
假如说跑步是 “单兵作战”,那马来西亚的自行车爱好者便是 “城市游击队员”。6.78% 的参与率看似不高,但考虑到这儿的马路几乎是摩托车的全国(吉隆坡摩托车保有量超 100 万辆),能在车流中杀出一条骑行路,肯定是真爱。
大马人对自行车的酷爱,带着点 “量体裁衣” 的才智。在槟城,自行车道沿着乔治市的老大街铺开,骑过百年骑楼时,还能闻到近邻咖啡店飘来的烤面包香;在沙巴的亚庇,骑行者会沿着神山(Mount Kinabalu)脚下的公路行进,一边蹬车一边看云雾在山顶旋绕。最硬核的是 “折叠车党”—— 他们把车折起来塞进捷运(MRT),到了城外再打开,完美避开市区的 “交通混战”。
当然,自行车的 “高光时间” 还得看赛事。每年的 “环兰卡威自行车赛”(Tour de Langkawi)可谓东南亚版 “环法”,选手们骑着车穿越兰卡威的红树林和海滩,观众则在路周围举着 “加油” 牌,趁便往选手口袋里塞巧克力。2016 年,本乡选手阿兹祖尔哈斯尼・阿旺(Azizulhasni Awang)在奥运自行车凯林赛中摘得铜牌,成为大马体育界的 “国民自豪”—— 他的故事被改编成纪录片,片名就叫《从吉隆坡街头到奥运领奖台》。
风趣的是,自行车还成了 “环保 + 炫技” 的结合体。吉隆坡的 “复古自行车沙龙” 成员,会骑着上世纪的英式单车参与集会,车把上还挂着藤编篮,里边装着克己的 kuih-muih(马来传统糕点);而年轻人则热衷于 “死飞”,在黑风洞(Batu Caves)的盘山路上扮演漂移,吓得周围卖玉米的阿婆直念 “阿拉保佑”。
或许有人会说,马来西亚的运动热,不过是 “美食过剩” 后的补救措施。但当你看到落日下,羽毛球馆的灯火亮起,公园的跑道上人影绰绰,自行车铃声在摩托车轰鸣中仍然洪亮 —— 你会理解,这儿的人们不是在 “对立” 美食,而是在享用 “吃得多,动得更欢” 的平衡术。究竟,能把运动变成像喝拉茶相同天然的事,大约只要大马人能做到了。